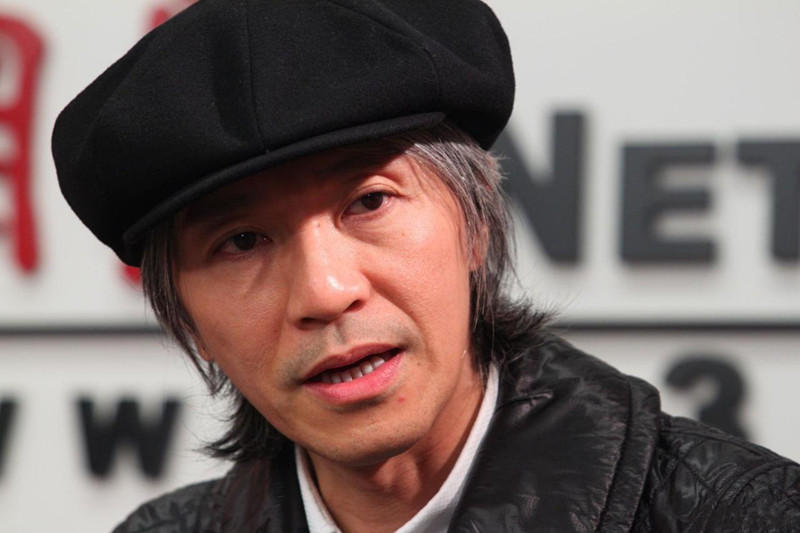阿微木依萝散文《木里记》(外一篇)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8年第五期
- /
- 作者:阿微木依萝
- /
- 2019-05-24 11:54:01
- /
- 24
- Views
竹林里的麻雀
它们飞到竹林里的时候是黄昏,在黄昏里开了一个会,次日的清晨,鸡叫两遍时又来了。昨日的到来,是为了一个集体的约定吧。它们约定以后就住在竹林里。
这些细小的麻雀——我只能用细小去形容它们,当我的奶奶从草房子的矮门里走出来,我就指着它们喊:看,它们像黄豆一样!
这个村子是孤独的,甚至,我作为一个不大的孩子,也会在某个时候感觉到心慌。这些山,水,石头,泥土,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树和草,在黄昏来临的时候,都罩着一层薄薄的雾。——不仅是下雨才会有雾,在高山环绕的村庄里,太阳落山以后,雾气便一点一点上来,直到它们变成夜晚的黑。
我有时找不着玩乐的游戏。许多游戏都玩腻了。在晚上,更是没有什么意思。麻雀在这个时候都睡了。它们睡得早,起得也早。
有那么几个无聊的老人坐在黑漆漆的院子里聊天,聊那片枯死的庄稼,或者,聊那只昨晚不知怎么死掉的猫,聊到动情的时候就落下几滴看不见的眼泪。她们到了这个年纪,心里只剩慈悲。
母亲的鞋垫要在傍晚才有时间缝补,还有奶奶,还有三婶,还有我的大伯母,她们像约定好的一样,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来到竹林边,一起缝补。她们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吵架了,也许为了一只鸡蛋,也许为了谁多给谁一把米。
奶奶是村里唯一清闲的人。她有时从竹林里突然钻出来,手里握着一只鸡蛋。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钻进竹林的。我感觉奶奶比我更会玩游戏。
奶奶和我有时在竹林里相遇,彼此都要大吃一惊,因为都在认真找鸡蛋,不清楚对方什么时候进的竹林。
竹叶实在太厚,除了用眼睛,还得用手。当竹叶翻遍了也没有鸡蛋,祖孙两人才心甘情愿从竹林里钻出来。
出来要快快地打水洗脸,洗手,洗脖子;竹叶上的竹毛痒得人难受。
竹林里的麻雀在黄昏最是吵闹,但也有闭嘴的时候,比如竹林下的女人吵嘴了。
当然也有男人吵架的时候。男人吵架只是干吼,吼完就走。如果要打架,也是打完就走。他们很干脆。那不干脆的必是醉鬼,他不与任何人吵架,终天躺在竹林下,咒骂,呕吐。
春天是这个村落的忙日子。女人不在家,男人也不在。只有几个小孩孤零零立在某个地边,无所事事。春天没有什么好玩,除了去山林把开得最好的山花一朵一朵掐掉,把那些刚刚冒出芽的嫩草一脚踩回地下,真是没什么事情可做。
“这娃儿真是坏透了!”——如果得不到大人们这样一句责骂,花就是白掐的,草也白踩了。
麻雀似乎想着搬家,在夏天的时候,我看它们全部飞到水井边的一棵水麻树上,那么小的树,居然可以站满它们所有的成员。它们说话的时候,嘴里似乎含着一口泉——咚咚咚,然后是——丁丁丁;也许我形容得不对,但这没什么关系。那些我听不懂的话,就从树叶的枝桠间漏下来。
秋天是母亲不得闲的季节,她要把收回来的粮食都晒在院坝里,然后派我站在那里守护这些粮食,她去坡地里继续忙碌。
麻雀在这个时候就从竹林里飞下来,它们落在院坝里的苞谷子上,看上去,它们不比苞谷子大多少。滑稽得很,它们居然张大了嘴巴,想把根本不能通过它们喉咙的苞谷子吞下去。
对于这些小贼,我只是看着。反正它们最终不能偷走一粒苞谷。它们最终会可笑地站在那里着急惊慌、又似乎带点羞愧地尖叫。
母亲让我守护这些粮食,以为我是个精明的孩子。她错了。我是个稻草人。假如老天爷跟我开玩笑突然下雨,我不会把晒着的粮食盖起来,我会像稻草人那样,只是忠诚地站在院边,实在受不了雨水,才会退到屋檐下。
母亲只让我看着场地上的粮食,除此,她没有交代别的事情。她不交代的事情,我绝不自作主张。
有一天我的奶奶和大伯母吵架,她们分别把自己栽种的南瓜从地里摘下来砸在地上,然后指着树上的麻雀骂,说,就算是麻雀,也有心肝五脏,人就这么无情无义么?
麻雀是无所谓的,当它们看惯了这个村子里的人的性格和生活,也就无所谓地长久居住下来。
有时,我羡慕它们有翅膀,可以飞,可以在比我高的竹林上跳来跳去。但不是长久的羡慕。
我有时候也会糊涂,我想不明白麻雀是不是有耳朵,当它们被骂的时候,它们毫无反应地住在竹林里继续歌唱,只有竹竿扫在它们的尾巴上,才大祸临头地惊叫着飞走。
月色明朗的夜晚,麻雀似乎也懂得赏月。它们在竹林里低声轻叫,声音就像草地里偶然滑落的露水,这声音不往地上落,也不往竹叶上落,它们原还落回麻雀的喉咙里。麻雀卷进喉咙的声音,仿佛是一个轻柔的赞美,它们不大声唱出这个赞美,只把它卷在舌头底下,好似一颗什么甜蜜的东西,往舌下一压,把那丝甜蜜吞下去了。
我也有自己的自私。我还是个孩子,我的自私是天真而粗暴的:我用竹竿扫开它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