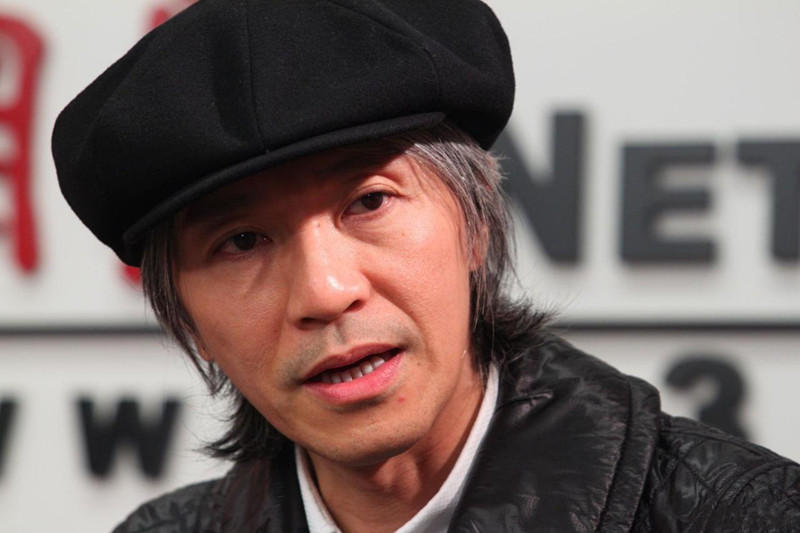古里拉达的狮子山(组章)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7年第一期
- /
- 作者:吉布鹰升
- /
- 2019-05-24 12:17:33
- /
- 24
- Views
编者按: 去年底,四川省作家协会为全面推进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,充分展示全省作家“深扎”活动成果。凉山州作家协会报送了5篇(首)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小说和诗歌作品,他们分别是俄尼·牧莎斯加(李慧)《淡出》(长诗节选)、英布草心(熊理博)《尘陋》(中篇小说)、俄狄小丰(蔡小锋)《走出萨河》(短篇小说)、吉布医生(吉布鹰升)《古里拉达的狮子》(散文)、阿克日布(阿克鸠射)《悬崖上的村庄》(报告文学)。这些作品都是凉山人自己写的作品,从不同侧面的展示了“凉山”的人和事,切实做到了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的作品。我们从这一期起,将陆续刊登,以飨读者。
古里拉达的狮子山(组章)
□吉布鹰升
狮子山隐没云雾深处
3 月28日下午2时,坐上了从昭觉县城开往古里拉达的中巴,一路上,我们随汽车颠簸着。车窗外,挂在天空的白云,有时一绺绺的,往各处飘去;有时是一大朵一大朵的,重叠成了云峦;有时像是雪白的蓬松的棉絮,如果可以摘下来制成毡子多漂亮呀;有时如一根根的细丝,随时都会被风吹散而了无踪影。云就这样无时无刻变化和流动着,烘托云的背景是深邃的天之蓝,那种蓝,或是淡蓝,或是湛蓝,或是蓝莹莹的,给人的心境也不同,尤其是那种蓝莹莹的天空,看起来令人心情十分愉悦和轻松,此刻仿佛所有的俗事都烟消云散了。
这个时节,山上生长的草木,除了一些松树和常青树,都是一片枯黄色的,其间也不时露出了点点的新绿。路边,一两块零星的燕麦地,长出了嫩绿的新茎叶。再过一个多月草木欣荣,山地化为葱郁的景象,散发出新鲜的气息了。那时,山里的空气是别样的清新,在大城市里最富有的富人也享受不了这样洁净的空气。所以,山区自有它的优势。尤其是晴天,在蓝蓝的天空下,美丽的山景和空气令人流连忘返。车上有族人在交谈,有时谈得很是兴奋。我的心里不时想像着我们要去的狮子山的景致。
有人指着窗外,为我介绍绵亘的山脉,说那是黄茅埂。听说,那里夏日的风光很美,它令我多情的向往。什么时候,我能到达那里,饱览它的美景呢?车到了古里且莫乡,此时,夕阳将要收尽余晖。
这里是诗人兼登山者阿说尔日的故乡。他和我一样,喜欢融入山野自然,我们下车后,把简单的背包卸下放在他的父母家。然后,来到乡中心校背后的悬崖之上。对岸是深深的峡谷,望不到谷底。峡谷像是刀劈斧削而成,是远古的冰川运动的啃噬形成的吗?这是大自然的杰作。望着峡谷,我们的脚步颤巍巍起来。
狮子山梁就在远处,那里积了点点白雪,时而被一绺绺的灰云隐没,时而又露出了几座山峰,远远望去,几座山峰相隔很近,但其实它们相距很远。有时,山峰之上露出了淡蓝的天空,我们便惊喜起来,心里祈愿上天保佑明天天气晴好。
转身回去,四山渐渐朦胧。这里的人们每天面对苍茫四山和熟悉的天空,生活单调枯燥。可是我第一次来,有陌生的新鲜感,于是,吃了饭,我和尔日又来到公路漫步,就在我们说话间,东山朦胧之上有一团淡淡的白色光晕,那团淡淡的白,洇染扩散,轮廓越来越清晰。哦,那是月的升起,它的升起,多么不容易。我定睛观察着,它奋力地往上爬,往上爬,终于露出了脸,光亮由柔和变为皎洁。便似乎以呼吸一口气的工夫,瞬间露出半张脸。就在我们说话间,就在我一秒秒数着时间的时候,它全然露出了脸。月亮是多么皎洁,浑圆。我看了看手机,时间刚好过了一分钟,就在这会儿,它又悄然离开了山顶,似乎被大自然无形的手托举起来。
星星两三点,在浩渺的太空忽闪着,大山是寂静的,仿佛令我一下找回了真实清醒的我。一个人只有远离人群,才能不迷失自我,才能审视和享受孤独寂寞里的那份清醒和真实?没有在空旷渺茫的山夜里,就不觉得一个人的荣辱和哀伤都渺小如尘。大地上栖息的生灵,包括山林里没有睡着或是即将睡着的鸟儿,一切归于宁静了。夜的空旷寂静,荡涤着我们的心灵,让我们和夜晚一样坦荡空明。
晚上,我们喝着酒。尔日的父亲,酒意微醺时,一再对我们说,“狮子山顶很冷,你们会被冰雪困在里面的。”他觉得他的儿子和我的行为不可理喻——待在家里好好的,何苦去登狮子山呢!他的担心和劝告让人觉得狮子山遥不可及。我对他解释,“我俩带了干粮和水,还有帐篷。”据说狮子山海拔也不过3800多米,话虽如此,我们还是担心的,比如遇到蛇,遇到下雨和打雷天气等。
临睡前,出来解手。皎洁的月亮依然挂在夜空,月光仿佛和大地私语。投宿在乡政府招待所,世界寂静了,只听见外面自来水龙头的水哗哗哗流淌。因为睡得晚,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大概凌晨时,做了一个噩梦,说是我的脖子被人掐着。在梦魇里醒来时,我担心明天上山的事情。
苏巴古河潺潺流去,我们走在狮子山
3月29日凌晨六时三十分,我被尔日叫醒。上了厕所时,月亮挂在了西山上空,它被一抹红云衬托着,忽而隐没云间,忽而又露了脸。
一会儿,便听到了喜鹊醒来时的叫声。我们背上简单的行囊,走上了公路。路边的树,远处的山色,轮廓渐渐明晰起来。
那一轮月亮,圆圆的,挂于西边上空。我们转过公路,月亮刹时沉了下去。鸟儿陆续醒来,那是新的一天,它们似乎问候我们“早安”,问候大山“早安”。东山轮廓也越来越清晰。天空和大地,随着我们脚步的前行,越来越明朗。我回望太阳将要从山岭山峦升起的方向,又看了看时间,已是凌晨七时十几分了。为了这次旅行,我专门查找了电脑网络上的昭觉天气和日出的时间,说是日出为早上七点二分。我们又走了一段时间,附近有农民荷着锄,往地里走去。他们很好奇地望了我俩。我俩一边走,一边聊着。太阳依旧没有出来。于是想到太阳爬上这片山,阳光照射在山沟里是多么不容易。经过了一个村子,附近的林子传来鸟儿清脆的叫鸣。村人三三两两,在村子的土路上搭讪。
苏巴古河潺潺流去。它并不那么清澈,幽幽地碧绿着。但是我们谁都能想象一年四季里它或是清澈见底,柔和如绸缎;或是浊浪翻滚,汹涌澎湃的不同情形。它从何处来,又流向何处?这像我们渺茫的人生多么相似,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从何处来,死后又走向何处?但是,人有了信仰,便不再迷茫。河流是否如此呢?
经过河上的一座石桥,沿着一条崎岖的陡峭山路而上。此时,阳光已经照耀了我们对岸的山峦丘陵。我们的视野渐渐开阔。在一个村子上方的垭口歇下时,附近,野鸡“嘟嚯……嘟嚯……”的叫声,还有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鸟儿鸣叫,传递着按捺不住的春之气息。这里山民的房屋,一律灰瓦土墙,已经很难见到诺苏人先祖居住的瓦板房。往西望去,那里一条条时隐时现的山路伸向远方苍茫的群山。一旦有山路的地方,便有村落。就这样很多人来了,又走了。最终,只留下群山的孤独和人生的长叹。往上走去,山野的气息越来越浓。路边的那些石头和树木,令我回到了故乡的感觉。这里遍布丛林,它们的生命比我还漫长,我还没有出生前,它们在那里,将来我离世了,它们依然茂密。所以,仅从这一点看,我敬畏它们的生命。有一截斜坡,留下了很多树桩,遥想以前高大的乔木丛林多么茂盛,它们曾经庇护了天空,庇护了大山。当失去这些树林的时刻,天空伤感,大山也落泪。突然,一只灰色的鹞鹰在半空盘旋了一阵,另一只从那边飞来。两只鹞鹰追逐嬉戏,时而盘旋,时而俯冲,时而上升,时而尖叫着,然后,双双飞落隐没于对岸的枯草坡,它们演绎了一曲大山浪漫的春之恋。
一朵花开在了垭口的草丛里。它绿绿的茎叶衬托着淡淡的蓝色的花儿,显得孤零零的寂寞。我们走过去,附近同样的花零星绽放。于是,花儿不再孤独和寂寞。一缕春光照耀,它们便不顾霜雪的凌冽,在寂寞清苦里绽放生命的精彩。
我们把背包卸下,立刻欣赏山景。这带山脉就是狮子山了。现在,它的众多山谷沟壑袒露在眼前,然而远处是薄薄的雾霭笼罩,或是晴岚弥漫,山脊时而云雾缭绕,时而露出了白白的雪。太阳时而藏在云后,时而露出脸。我情不自禁地说,“狮子山,我终于来了。”这是我等待了多少年的梦想呀。这梦想何其遥远,然而它真真切切地实现了。山以宽广仁慈的胸怀容纳了我,我是为自由而漂泊流浪它怀里的一朵云吗?
爬过陡峭的岩石,穿越茂密的原始森林
为了赶时间,我们只是在那里休憩了一会。然后,继续朝着陌生的原始森林出发。据说,这里,每一座山峦山岭都有森林。那么,狮子山脉的森林,你徒步是无法用几天的时间把它们一一穿过的。所以,我们只有选择最近的前方森林。我俩把事先备来的土黄色的雄黄粉抹在鞋、裤子、衣服上。据说,蛇嗅到它的气味,便远远地躲起来。不过真不知这是否应验。听说,山里有一种会飞的蛇,冷不防它会朝你飞来。这让我想起了读过的一个短篇小说,讲的是生活在竹林里的一种蛇,母蛇平时性情温和,可怀孕的时候突然性情暴躁而攻击人。这事是多么蹊跷有趣呢。林中空气湿润,时有鸟儿叫鸣。同伴尔日走在前,我跟在后。我们沿着林间小路,一边走着,一边观赏路边的树木。踩上柔软的黑褐色的泥土,鞋子不时打着滑。茂密的树林和竹林里,不时现出被砍伐后留下的树桩,已成了朽木,黑黑的,你用手去触摸的地方,松软得像细沙一样。也有被砍伐后未被搬走的废弃的木头,也是有了朽意。一棵粗状的树木,诺苏人叫它“格尼”,树干的直径一米有余,虬枝张牙舞爪如一个高大的舞者,它的历史或许有上百年了。一种索玛树,树干犹如手臂粗,绿叶上衬着一两朵鲜红的花朵。突然,一阵刷刷的声音响来,我们担心遇到野兽什么的,便对山大声吆喝。一会儿,那边有人唱起了山歌,才打消了疑虑。渐渐地,我们和两位伐竹的牧人相遇了,他俩各背着一捆竹子,其中一位脸黑黑的。我们搭讪了几句。他俩是山下的村民,平时放牧山上。我们问“那边还有人吗?”他俩说,“还有一户人家。”“那边有住房吗?”“有,你们可以住在那边。”但我懵懂他们所说的那户人家的具体位置。我们朝着相返的方向走去。我不知道他俩背来的竹子是从哪里砍伐来的。尔日说,是从放羊的地方背来的。可是,极目望去,却看不到一只羊。
这是一块巨大的岩石,呈灰白色的,间以点点墨黑,上面覆盖了斑驳的青苔。岩石有一处凹槽,湿漉漉的,晶莹的水如挤出的乳汁一滴一滴落下,落在洼地的声音,显得多么安静。岩上有一棵黑黑的树木,倾斜成五六十度的角冲天而长,树干如腿粗,高两米有余,光秃秃的枝梢,看似有了几分朽意。生命是多么离奇呀!它的种子落在岩石缝隙里,便借着日光和雨露,吸取岩缝里的土壤营养,艰难又默默地长成一棵大树。它承受了无数时日的风雨交加,然而不屈不挠地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。那理想是充满阳光的天空,也是自我生命的张扬?在另一处打滑的黑色的岩石上,我们只能蹲着慢慢往下爬,进入一条河沟,往上爬去,上面也是一截岩石坡。岩石边上,一棵树上用绳子吊了一根藤。我谨慎地一手握住藤,身体前倾,迈了一步,然后紧紧地抓住岩石棱角往上爬。我往回看去,脚步颤巍巍,眩晕起来。于是,我丝毫不能松懈,怕一不留神滑下沟底去。终于,登过岩石,我松了一口气。这是一片洼地,疏疏朗朗的一片树林,一律光秃秃的没有叶子,呈现一派傲然风骨。有的树上挂着长长的绿色的松萝,有的树上缠着粗壮的枯藤。一棵粗壮高大的索玛(杜鹃树)骑在一块岩石上,从石岩缝里长出,盘根错节伸向岩石下的土壤里。一棵手臂粗的索玛,另一棵暗红色的“格尼”(红桦木),同时长在一棵粗大的朽木上。一棵参天大树从另一棵朽木的怀抱里长出。这里,各种树木自由生长,却也相互竞争激励。如果,走入那些没有路的丛林里,真不知其他的树木又多么神奇。可惜,我们仅仅是路过者,无暇也无胆量闯入那些丛林里,那实在是冒险的事情。据说,狮子山的丛林野生动植物丰富,动物有野猪、黑熊、岩羊、狼、雉鸡、白腹锦鸡等,植物有楠木、红豆杉等珍稀树种,还有贝母和珍稀的兰草等,保护这里的生态是何其重要。解放前,这里人迹罕至,国外的探险家想登临这块未开化的秘境,也种种原因最终不得不望而却步。
穿过这片原始林,我们差不多用了三个小时。坐在山冈枯草坡,回望原始林,前方有一条溪流从石岩上潺潺倾泻而下。溪水流向何处去呢?从山势和地形来看,它应该流过我们走过的路,然而一路上并未看到河流,这使我们百思不解。溪流附近,丛林里杂生的高大的索玛树尤为惹眼,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到绽放的时间。我俩吃了饼干和喝了水,休息一会,体力恢复后继续朝山顶爬去。尔日说,真正的狮子山就是我们背后的这座山。人们不知道从哪一个角度看它觉得像一头狮子的?因为从我们这边望去,它根本不像狮子。
千年一遇的云海
牧人的住屋,建在山冈斜坡上。牧人就地取材,用石块垒筑墙,上面搭起木梁,盖了杉木板。它们多年无人居住,大多废弃了,有一间能够勉强住人。我们把门“吱呀”打开,堂屋狭小,地面因为前几天下雨的缘故积了薄薄的水。楼层铺了枯草,算是寝卧处,旁边有一杆猎枪。牧人屋简易沧桑,可想而知,牧人的生活多么清苦,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时候。每年六月,山下的牧民就把羊群赶往这里敞放、露营。也有一年四季把牛羊放在山上的。然而,此时却见不到一个牧人。即使大喊一声,大山寂寞,空荡荡地没人应答。
啊,登上山巅了。对面我俩穿过的几座山,山脊时而露出了白白的积雪,时而云雾缭绕。一绺绺雪白的雾朝我们这边涌来,一些丝状的雾从我们身边擦过。我们几乎能抓住它们,然而一捏上手却空空的。不知何时,云雾遮住了我们回去的路,山也被雪白的云絮填满,形成了多么壮观的云海。它不断地变幻,云絮弥漫蒸腾,气象万千,把它的奇幻美妙展现给了我们。云海之上,天空是蔚蓝,或淡蓝的。把这千年一遇的狮子山的云海留在你的记忆。云的无时无刻变化游动,这是大自然精彩的杰作。站在山顶,仰望或俯瞰着云海翻腾的画卷,人生里能有几次这样的遭遇。
我回过身来,一只黑色的苍鹰大概距我不到一百米处的那最高的山巅自由飞翔。它的滑翔是那么平稳,渐渐沉降,然后缓缓俯冲而下,消失在了那座山后。它的消失,是瞬间,令我多么遗憾。它的飞翔,把自由画在了天空,成了瞬间的永恒。此时,一绺夕阳照耀山顶一隅,一会儿就消失在了茫茫云雾里。夕阳将要西沉了。明日清晨,我能否有幸看到太阳又从山底爬上来的壮美景致呢?狮子山的日出,我相信它让无数人顶礼膜拜,让那些世俗的欲望烟消云散,让心灵得以洗礼而变得单纯洁净。它是生也是死,是瞬间也是恒久。它让万物平和安详,本能地呼吸大山芬芳气息,保持自然生命的活力。
走过飞鹰消失的山巅,便见一圈栅栏,栅栏是围来做菜地,还是当羊圈呢?我们终究猜不出它的用途。我们已经来到了山梁,这里往东方沿伸的山脉、山峦,现在云遮雾绕,属于雷波县辖区的狮子山。我们在山顶一低洼处,开始搭帐蓬。风呼呼地吹着,帐蓬的支架经不住风的几次折腾,一次次被掀起,无法在此露营。此时,雷声轰隆隆,一阵阵从不远处的浓雾里传来。雨淅淅沥沥,我们担心夜晚天气更加寒冷。于是收起帐蓬,决定绕过山脊,返回山下的那个村庄。
雨雪纷纷,暮色苍茫
夜宿山顶,风雪雷电交加之夜
刚走上一截缓坡,雨雪纷纷而下,雷声一阵阵从远处逼近。为了避雷,我把手机关闭,把伞也折叠起来,任雨雪纷纷落在身上和头发上。越往上走去,缓坡上的积雪越难行,有的地方没过了膝。云雾迷茫,渐渐地暮色越来越重。路似乎消失了,几乎无路可寻了。尔日说,他小时候曾放牧这里,2011年也来过。然而,我们一时找不到路的痕迹了。尔日冲着大山大喊几声,希望得到有人的回应(听说,离这儿不远处的山下住了一户牧人),然而,只有雪落的窸窣和我们的走动声。那刻,我们越慌张,越陷入绝望了。最终,凭着感觉,翻过一座岩石,又直上,达到了另一座山巅,这里有一地标,形似火塘。据说这是狮子山山梁最高处,可又找不到出路了。往一斜坡走下去,然而路又消失在了灰蒙蒙的积雪里。暮色苍茫,雷声铿铿镪镪,在我们附近炸响。我们只能返回躲在身后的一块岩石下,拉开帐蓬,躲在了里面。不到一会儿,雨雪“沙沙”落在了帐蓬上,电光闪烁,有几声沉闷的雷响在附近的山头。
一阵阵轰隆隆的雷声,让山里的鸟儿和其他动物都惊惧隐匿起来。雷电显示了大自然的威力,使人们不得不敬畏自然,感到人自身的渺小和脆弱。在海拔3800多米的山顶上,是无人居住的。它属于生活在这里的那些野物,人类只不过是偶尔的闯入者而已。山顶上天气变化无常,中午蓝天白云,现在已是乌云凝重,一片灰蒙蒙的世界,似乎是世界末日了。我俩躲在帐蓬里面,各自蜷缩成一团,不到一会儿,从帐蓬漏下来的雨水浸湿了我的头发、裤脚、鞋子和脊背,我垫坐的背包和那件羽绒服也被打湿了。尔日把事先带来的那张防潮垫蒙在我们的头上。此时,帐蓬内因为我俩的身体散发出来的热气和呼气,再加上我把尔日买来的那件小毛毯盖在了膝盖上,我并不感到寒冷。外面,雨雪纷纷。如果没有帐蓬和那张防潮垫,以及毛毯,今晚我们会被冻僵。尔日说,冬天,狮子山冰雪曾冻死过路人。现在,我们最担心的是沉闷的雷电。于是我们把电筒也关了,暗暗祈祷,心里想,“雷电不要往我们这里劈来,乌云快散去吧。”一会儿,外面沙沙响,可以感觉到风吹着雪,吹着我们的帐蓬。尔日不无担心地说,我们会不会连同帐蓬被掀翻,或是不小心跌落滑下悬崖?我说,不会的,风力并不能够吹动我们。只要我俩时刻注意,身体不要往下滑。虽然我们运气很坏,不过下雪倒是比下雨好。如果下起暴雨,今晚我们全身被淋湿,甚至会感冒的。更危险的是,万一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是最恐怖的事情。雷声停一阵,我们立马打起电筒,打开手机看时间,此时,已到了晚上十点过,然后又立马关上手机。雷声不时一阵阵响在附近的山头,雪依然不住地下。我们把命运交给上天,任它主宰我们的今晚。网络上天气预报说是昭觉今夜阵雨或局部多云。昨晚多云,月明星稀——今日上山,我们都说在山顶露营,观赏月色星光,聆听清风虫鸣,是多么惬意呀!现在,这种浪漫的情致被我们求生的欲望消磨殆尽了。雷声,一阵子打在我们附近的山头,雪依然纷纷扬扬。在雷声带来的恐惧里,不知度过了多长时间,渐渐地雷声远去,我便开始逗趣地说,“咱俩今晚露营是过原始人的生活。只是我们住在帐蓬里面和穿了现代装而已。”尔日嘿嘿地微笑着,“是啊。”然后,我俩同时想到了白天见到的那间牧人屋,要是早知道这样,不如到了山顶就应该返回那座牧人屋——睡在楼层的枯草垛里,拉开帐蓬,多么安稳又暖和。冷了,也可以拾柴火烤。有时,我也抱怨责怪尔日,不像曾经来过这里一样,竟然也会迷路。他望着我一直沉默着,心想“你不是主动说要登狮子山吗?”其实,也不怪他,怪我俩都胆大,另外抱了侥幸心理,以为多云的夜晚,月明星稀。露营在外面除了具备必要的生存知识,了解当地的气候是必须的。午夜,风雪雷电更厉害了。尔日担心地说,“吉布老师,咱们现在就走吧,如果大雪封山,明天我们就走不出去了。”我望了他,说“走吧。”刚把帐蓬的拉链拉开,伸出头来,用电筒扫射了前方几下。外面,一片朦胧的灰白的世界,寒风裹着雪一阵阵吹打在我们的脸上。我劝住了他,“不能走,咱们这样出去,会被冻死,或是摔下悬崖的。况且,雷还在打,又不能打电筒。”我们神色慌张了一阵子,然后才渐渐冷静下来,安然地坐在帐蓬里。风雪渐渐小了,但是雷声依然轰隆隆响。我们又看了看手机,已经是凌晨一点过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呀。我们来到这里已经度过了五个多小时。再熬五个多小时,就天亮了,可是后来的时间很漫长,我们打起手电筒,每隔一阵,便数着时间。我们也丝毫不敢打盹一会,因为帐蓬里的空气太稀薄了。尤其尔日的呼吸急促,大概是缺氧的原因。他把帐蓬拉链拉开,伸出头呼吸一下,然后又把头缩进帐蓬内。外面,一片寂静,除了雪粒落在帐蓬的声音,还有似乎什么野物踩上雪的声响。我想起了山里有野猪、狼等动物出没的时候,担心撞上它们,受到袭击。此时,我想,抖动帐蓬,拍掉落在帐蓬上的雪,发出的声响会吓跑那些动物。不过,我们最担心的还是明天如何走出这片山的事情。于是,心里暗暗祈祷,明天早上到中午的这段时间,即使下雨,也不再打雷。只要回到山下的那个村落,我们就安然了。我们几次打开手机,几次看了时间,然后等待着天亮的那刻。从凌晨四点半到五点,又过了五点半,帐蓬外的雪光从朦朦胧胧渐渐一点点明亮起来。尔日说,凌晨六点时他先去找路,再来喊我。我并没有同意,说,“万一迷路,走失了咋办?”
寂静的雪野
3月30日凌晨六时,我俩钻出了帐蓬,我把那件毛毯披在了我的背上,外面再穿上了外套。这样,我的身体感到了暖和。尔日收拾好了帐篷,“说,山顶下来大概一百米处有一些石头。找到这些石头,就很容易找到出路了。”绕过我俩住的岩石,那里隐约有一条白雪掩盖了的小路(其实,看不清是路,是我俩的感觉)。我们顺着小路(其实算不上路),往前方寻去,走了一段,尔日感觉不对,就转身,往山顶地标处找去。此时,我的手机响起了闹钟,已经是六点半了,天也渐渐亮起来。从地标处下来,我们又回到了走过的路,根据直觉,应该这个方向错了。往回走,再向下,尔日说应该是这里了。我说,你确定了吗?他又走下去,说,应该是这里,确定了。原来,那里有几块黑色的大岩石,有几根木头搭起的架子。他说,这是他以前放牧这里时住的守羊棚。此时,天大亮了。狮子山的云海尽现在我们眼底。山顶露出了一片白皑皑的世界。尔日要取出相机来拍照。我指责了他,“你还有时间去拍照,万一又下雨、打雷咋办?”他很冷静,嘿嘿地笑,“没关系的,不要紧。” 我说,“你不怕,我们昨晚都怕够了。”——其实,我实在没有道理,如果不是我要来,他也没有这一遭的。他或许想对我说,“你这人太怕死了。”
这些雪白的云,什么时候聚在那里,成了云海。云海遮住了广袤的森林和山岭沟谷,除了山脊以上到山顶露出了一片白皑皑的雪。几声鸟鸣,清晨无边的寂静。我们的脚步声也消融在这无边的寂静里,心灵受了震撼和洗礼。世界的每个时刻,哪怕是昨天的一片树叶,今天醒来也多么不同。它经历了昨晚的风雪洗礼,会变得更加的清新和朝气蓬勃。狮子山的风雪之夜,和今天铺上云海和白雪的壮观也是多么不同。这里的每一棵草,每一棵树,每一座岩石都春潮涌动。
我们渐渐翻过一道山梁。前方,传来一只云雀的声音。我暗想,云雀的叫声,预示不会下雨。又翻过一道山梁,往下走去,走入一片开阔的洼地,那里有一些黑点。尔日说,“那是一些牦牛。牧人,是个老人,吉克姓氏的。”他远远地喊了那个牧人,“喂,吉克——阿普(老人)——”可是,天空空空的,没人答应。走近了,原来那些黑点是一些石块。记不清又翻过几道山梁几座山坡,艰难地走下山去。终于,来到了昨天我们上山时休憩的那个地方,那里散落了一些被牧人弃置的竹片。我们来过的这条路,在迷雾里,它依然让我陌生,此时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四十八分了。
在回村子的蜿蜒山路上,遇到一位牧人,穿着黑色的“佳史”和“瓦拉”,赶着一匹褐红色的马,马上驮着沉甸甸的袋子。他时而望了我,又时而望了尔日,问,“你们从山顶下来的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里下雪了吧?”
“雪很厚,昨晚雷也很大!”
“晚上睡哪里?”
“岩石下,睡在帐蓬里。”
我劝他不要上山,今天要下雨。可是他瞥了我们一眼,说“你俩慢走。”然后,继续往上走去,消失在灰蒙蒙的云雾中。也许,牧人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天气。
我安然地回到家里,回想起狮子山的雪路。那段经历,恍如梦境,又不是梦。这是我人生里不可多得的艰辛的一段山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