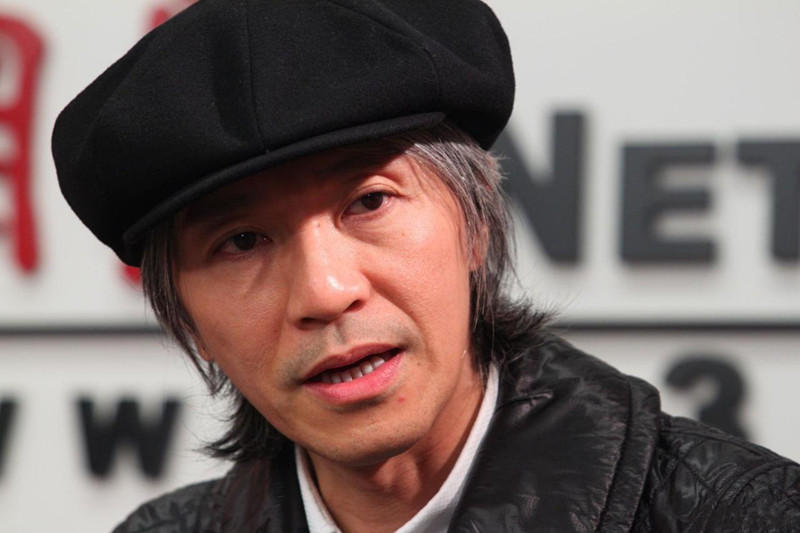阿微木依萝散文《木里记》(外一篇)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8年第五期
- /
- 作者:阿微木依萝
- /
- 2019-05-24 11:54:01
- /
- 24
- Views
木里记
我们要去木里。
头一天晚上,她像个真正的旅行家那样翻出她的背包,抖掉灰尘,往背包里塞入牙膏牙刷,毛巾和衣服,还有一双干活穿的平底鞋——她准备好了要爬山。她在常年居住的地方爬了五十年山,又准备去爬另一个地方的陌生的山。
她把脏毛巾拿去洗了再洗,生怕毛巾上的污渍泄漏了她的身份。她翻出压箱底的新衣服,那些衣服有的是我买给她的,有的是妹妹买给她的,还有的是她二姐买给她的,这所有衣服从前都不穿,像纪念品一样收在箱子里。
我看得出来,今天她不是我的妈妈,也不是我爸爸的妻子,今天她只要做一个简单轻松的旅人——住旅馆,吃露天餐,如果体力允许,她希望可以在野外搭一顶帐篷。
为了预先锻炼脚力,我们决定走山路去小镇搭车,用了七小时。到镇上已是下午,顺路去县城住了一晚,次日买票去西昌转车。
央宗和她的男友在木里车站已经等了很久。我们住在她提前定下的木里酒店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以“酒店”命名的旅馆。妈妈显得非常兴奋,她失眠了半个晚上。
木里以阴天迎接我们,平平淡淡的姿态,符合它长在半山上的性格。山势所限,它整体的区域比我出生的小镇大不了多少,许多地方正在修整,地面堆着砖块和水泥灰。
夜里幽暗的路灯下没有大城市浓雾般的霓虹。空气稀薄的夜街上,人们在灯下散步。他们低声说话,缓慢走路,就像山谷里往上吹拂的风在叶片上弄出的细碎响声。
央宗上班的时候,我和妈妈出去散步。木里的街道大部分是陡坡,从街这头走到那头,要耗去一定的体力。小型三轮车停在街道两边等客,后面塞着一块石头防滑。我们走在路上,时不时有人问要不要搭车。卖水果的摊子艰难地支在路边,包头巾的妇女穿着汉族衣服,但我一眼就能认出她是彝族。再有卖小饰品的人,那就分不清什么族了,他们大体一致的肤色和着装,跟彝人说彝话,跟汉人说汉话,跟藏人说藏话。
大概所有的小县城的白天都是一样的,谋生者占满了每一个角落。他们身上背着同样的标签:谦卑。勤劳。疲惫。顽强。
这里其实和别的地方一样。生活在哪里都是一个模样。即使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,人们也要像蚂蚁一样奔忙。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风景。我想这么跟妈妈说。但我没有说。这一次,我们是来看风景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别人怎样生活,之后,妈妈将回到农村过她的生活,而我再去过我浪子的生活。
第二天我们去了“寸多长海子”。它在卫星地图上是这个名字。从木里县城的弯路绕过去,沿着一条小河蜿蜒而上,直到县城被抛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,寸多长海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。
我并没有一下子看到那片长海子,进入我眼里的是玛尼堆和成片的松树林。天气晴朗,白云在湛蓝的天边流动,与松树林接近,看着像是从松林里升起来,然后再飘到天上。山包上风大,玛尼堆和松树上挂着的经幡将藏族人的祝福吹到远方。
长海子就站在我的眼皮上,伸手可及,实际上它离我很远,还不到五月,它被枯色的草包围。长海子周边的山势形成缓坡的样子,大大方方展开,远望像一片稍有凹凸的大平原。当然它不是真正的平原,所以在缓坡上你能一眼看见斜站在草地上的牦牛。说起牦牛,我总是认不清它,总将它看成大号的羊。央宗提醒了几次,妈妈也提醒了几次,我还是喊它羊。
康坞大寺在长海子的另一边,转过几个山包就到了,风马旗飘摇。年轻的喇嘛向我们走来,拿了酥油灯,然后领我们进寺参拜。
我是个不合格的信徒。我只能呆呆地望着门口那个磕长头的男子心生敬意。央宗的男朋友和他的同学,俩人在菩萨面前虔诚地磕了三个长头。接下来是央宗,也许为了教我怎样参拜,所以她并没有磕长头。她的手微微举过头顶,然后是嘴边,最后放在心口上,再弯腰拜下去。这一系列动作吸引着我。拜完之后,她眼睛柔和地望着我说,“你拜吗?”
我们点燃了酥油灯。妈妈取下了她的帽子。她向来是个虔诚的人,心中有佛,只是没有进寺庙参拜过。她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,成年累月在山中的土地上劳作,只熟悉山中的石头,泥土,风色和日月。
我们再回到长海子。母亲喜欢在山包上多待一会儿。我见过真正的大海,那是个十分丰富的地方:海边站着椰子树,树下有人在卖新鲜的椰子果,有人在海边卖烤羊肉,有人在沙滩上吹风。如果你在那里的任何一处歇脚,很有可能遇上一个向你兜售廉价珍珠项链的人。在那宽敞的沙滩上,有沙滩椅可以坐下来观海,你也可以下到水里去冲浪,只要你高兴,还可以在海边掏个窝把自己埋起来。海边常年有人。海从来不缺少观众。但长海子此时就我们几个站在山包上,非常冷清也非常舒服,在我们身边只有风和牛。海鸟从松林的顶端啼叫着飞向长海子上空。长海子和天空一个颜色。海鸟落在水面踏着云彩,那时阳光也照在海面上,水鸟收住翅膀停在长海子漂浮着的一团一团的“陆地上”,仿佛在欢呼自己是第一只找到新大陆的鸟。
央宗说,到了五月,海子上面漂着的陆地就会转成一团一团的绿色。它们本身就是由水草组成,漂到水上看起来像袖珍型小岛。
藏族人的信仰随处可见,山包上几棵矮树披着洁白的哈达,它们像四月的花开放在山顶。
妈妈迎着山风拍了一张照片。她的短发被吹到脸上,身板挺直,精神抖擞。在照片上你根本不能发现她已经是个驼背的老人。我可以从她沉默的脸上看出她的心思。她无法抑制的感动跑到她的眉头,平日紧皱的眉头此刻是舒展的,它们像音符一样跳开。还没有来长海子的那天晚上,她在旅馆的房间整理她的东西。她不知道穿什么样的衣服去长海子。她翻出红色的毛衣,一条深色的裤子,还有一顶新帽子。她把它们又一次摆在床上。
看着她瘦巴巴的脸,蜡黄的肤色,我想起朋友小康在西昌饭桌上说的话——阿姨,你好瘦哦,不过精神很好呢。
她确实精神很好,穿什么都精神。我对她说,你穿什么都好。我把那红色毛衣递过去。
她没有换上新衣服来看长海子,仍然一身旧装,站在山包上,她望着长海子周边的山林赞美那些她熟悉了半辈子的松树,也赞美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海鸟、白塔和哈达,以及飘在四处的风马旗。牧民的木房子让她大开眼界,她说她也想去做牧民。
“这里没有人跳舞,应该是没到季节吧?这个时候格桑花是不是没有开?我一朵也没看见。”她说。
我感到愧疚。五十岁第一次当旅人,这么晚的年纪却来早了,格桑花还要等一阵才开,跳舞的人要过一阵才来。
“我们等到花开再来。”这话说得很心虚,谁知道哪时花开,哪年再来。人总是在错过里满怀希望,又在满怀希望中错过和老去。
她一个人走到山包的另一边去了。她孤零零正对着长海子,时而抬眼望天,像一只孤单的海鸟。终于她坐在了地上,背对着海,背景碧蓝,像一片美好的回忆,可她左边是石头和枯草,右边也是石头和枯草。她是我见到的最美丽又最孤单的妈妈。我回忆起她二十八岁的样子。那时我还是一个孩童。我看见妈妈穿着白底碎花的衬衣,梳着两条辫子,手里端着一个撮箕,从地里给我摘来一些红番茄。她的声音温柔而年轻,她的笑容就像红番茄。多年来,我回想她的样子总是不由自主跳到她二十八岁的时段。
过了一会子,她起身,转身望着山包上的我。她远远朝我招了一下手,指着天边,大概要告诉我那里有一只海鸟飞得好像高过云彩。
我所站的位置,可以一眼看到山包下面的牧民区。他们的木房子低矮地站在草地上,央宗说,这些房子的抗震效果极好,冬天还很暖和。这几年为了方便牧民,减少四处游走的辛劳,在山顶建了许多木房子。我们来的一路上有好几个地方看到许多牧民。
长海子周围有几百头牦牛,它们像星星散落在地上,摇着笨笨的尾巴,一双短腿踩着草地,有的动也不动立在那里好几分钟,有的干脆躺在地上休息。其中一头牦牛独自站在水边,最后它走进水中,不很强烈的阳光碎碎地落在它周围,水珠被它的尾巴搅起来镀上一层朦胧的金黄。我将这个画面记在心里,如果有一天谁问我隐士是什么状态,我就指给他看这头牦牛。
离开长海子有万分的不舍。但我知道天下无不散之宴席,风景也是。三毛曾经找到了她的心湖,然后将心湖带走了。我也是。
我们从山包上往下走,央宗在草地上发现了一朵细小的白花。这朵白花正是那些枯草开出来的。它藏在草叶下,眼力不好或者不低头根本瞧不见。再后来我发现了更多的白花,妈妈也看见了。她一路低头寻找。这是她的格桑花。
一路沿着小河回木里县城。中途吃了点东西。傍晚,我和妈妈在木里公园逛了一圈。一人买了一只土豆坐在白塔面前的椅子上吃。这样子肯定有些傻。当时打着雨点,我们没有带伞,就着雨水将土豆吃下去。
“人一辈子就一个五十岁,我此生当中能来这里一趟,值了。”妈妈站到白塔前,挺直腰板,准备让我给她拍照。她身后是一棵开花的树,紫色的花瓣粘着几滴雨。
她拍照永远是一个姿态:挺直腰板,精神抖擞。不管是站在长海子还是公园的白塔前,换的只是背景,她始终一脸沧桑,但神态坚定。她很少在拍照时露出笑容。她的笑容非常少。或许她心中是有笑容的,但常年面对大山,面对大山上的土地和庄稼,时间长了,她的表情只剩下剔除笑容后的温顺模样。差不多所有山上的女人都和妈妈一样的神态,她们用这种近乎漠然的神态面对大山,也用这种单调的神态过完一生。她们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长海子,从来不知道藏族人将玛尼堆修在高山顶的松树林,将祝福和祈祷拴在风马旗上——她们一生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。
当天晚上,我们去朋友家里聚餐。妈妈显得十分拘谨。这个拘谨与我的疏忽多少有些关系。首次去别人家里不带任何礼物登门是很不礼貌的。而这种事情,粗心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。所以这次再犯我也表现得非常淡定。当然,在看到朋友家中有三个老人时感到一阵羞愧。我属于死鸭子嘴硬的人,低声安慰妈妈:没什么关系啦,大家都是朋友,应该不拘小节,再说现在不是季节,许多水果也不好吃。
吃完饭还没等到彻底散席,我和妈妈提前告辞了。又不带礼物还提早退席,是更大的无礼。但次日要搭早车离开,只能无礼到底。我们走路回旅店,晚间九点,路灯已经亮了,空气很冷。从朋友家出来的那条路一直是爬坡,坡度很陡,爬坡的时间用得比较长,好像要爬到山顶去的样子。这是我们在木里走的最陡的街道。之前酒店门口那条斜坡跟这个比起来真不算什么。很庆幸没有打车回旅馆,像这样的街道一辈子不走一回要后悔,何况与妈妈肩并肩,我们像两个得胜而归的老战友。
爬完那段陡坡,走到平缓的地方时,三天里熟悉的夜市摊子又出现在眼前。卖烧烤的人拿着一把夸张的大扇子对着炭火扇风。“来两串吗?来吗来吗?”他的声音像夜风轻微响在耳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