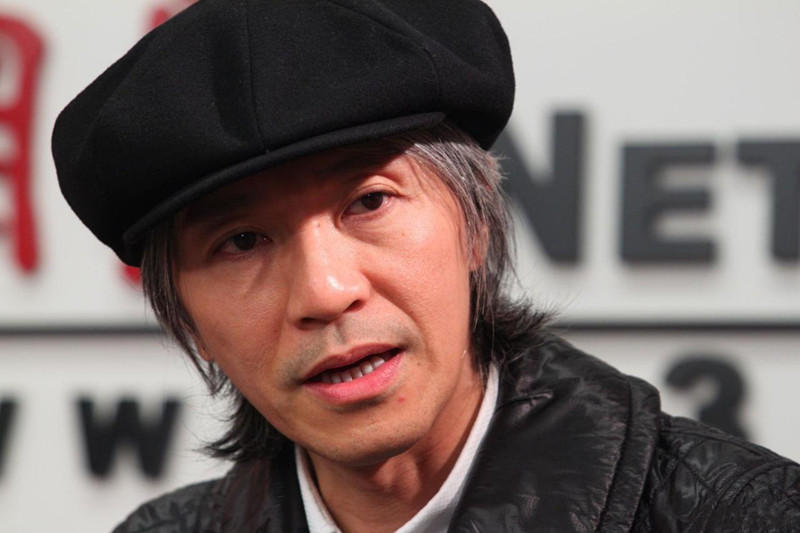古道苍茫 ——何万敏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8年第二期
- /
- 作者:何万敏
- /
- 2019-05-24 12:07:19
- /
- 24
- Views
进建昌城
我供职的单位在西昌古城的中心,走不了几步,就是古城往昔最为繁华的四牌楼所在。当然,曾经是地标建筑的四牌楼早已灰飞烟灭,我只是从老照片里一睹其黑白影像。和许多小城故事一样,今天的古城与新颖的城区两相比较,古老往往意味着凌乱而衰败。出门即是北街,向南经过一个十字街口来到南街,然后穿过大通门就算出城了。
记不清多少次,当我从城门洞下经过,往往产生一种“时空穿越”的奇妙感觉。我知道,曾几何时,凉山往往被一些外省人视为“不毛之地”,被贴上封闭、落后、野蛮的种种标签。殊不知,由于它所处的特殊位置,偏居中国西南,在地理上却是内陆与边缘的一个交汇点,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“最早”的碰撞点之一。在这个点上的西昌城,从古至今是许多条驿道、马道、公路、铁路的要地,它自然充当了部分中原人向南出入于云南,并再出入于老挝、泰国、越南、缅甸、印度等东南亚、南亚乃至西亚国家的地方。
通常而言,西昌天气最热的时候并非盛夏,而是4月底5月初的十余天。因为在一年当中,这里的旱季和雨季几乎各占一半,夏天虽然总体气温偏高,但雨水的密集冲刷了热浪;反倒是经过冬春长达数月的干旱,春雨姗姗来迟的那些时日,西昌竟有直奔入夏的炙热。
我记得2016年一进入5月的酷热却不是天气,而是复建古城墙时掀开的古钱币热。西昌在恢复重建古城墙时,偶然在大通门施工现场挖掘出大量古钱币,顿时引发民众哄抢。
毕竟只有一步之遥,得知消息的那个傍晚我赶到现场,只见工地开挖出的泥土与石块之上,人头攒动:有人手执电筒仔细翻寻泥土,有的则拿着一串糊满泥浆的钱币战果等待买主,讨价还价的文玩商贩于人群中穿梭,生怕漏掉眼看到手的大鱼,后来几天随着媒体的报道,据说还有来自成都送仙桥的大佬星夜驰来一探究竟。我没有资本倒腾发财,却担心文物流失总不是好事。与西昌文馆所的专家热线联系。对方说得明白,年号为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的“通宝”收藏价值都不甚高,如果你看到康熙、雍正的,品相又好的话,可以考虑。在渐渐暗淡下去的昏黄中,我悻悻离开还在旋转的人流。
文物专家们也不敢怠慢。他们请警方封锁了现场,仍然清理出187斤钱币。以后的鉴定结论是,从钱币上的满文得知,绝大部分产于云南宝东造币局(东川),其余少部分产于云南宝云局(昆明)和四川宝川局(成都)。史书记载,光绪十七年(1891年)五月二十九日,西昌东河爆发洪水,冲毁城墙二十余丈,西街、顺城街、大巷口等数十条街巷化为一片沧海。惠珉宫、五显庙、禹王宫、福国寺等庙宇荡然无存,田禾淤尽,倒流入海,淹良田二千余顷。出土钱币位于西街口打铁巷,“当年的钱庄或来不及撤离,最终被洪水淹埋”,专家分析。
那段时间,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件事,吸引着市民的好奇心。
一是随后不久“掏”出了800多米明代古城墙。西昌古城墙依据上百年前建昌古城图修复,发现一段长达800多米的明城墙,“城墙高达8米,超过了我们的想象”。西昌市原文管所长张正宁,天天在工地现场指导,他的解读是,东河经年的泥石堆积,造成我们今天站在城墙外看,似乎城墙是埋在地下的现象,“但以前肯定是远远高于地面的”。依此复建的古城墙由南门一直连通东门,并对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安定门加以维修,重建了门楼和瓮城。
二是修复古城墙时,不用水泥而专门熬制糯米灰浆,将三层不同材质的墙体接缝填充和粘连。第一层鹅卵石,第二层为条石,第三层是按原先规格土窑烧制的青砖,用去37万块。
重要的是,糯米灰浆钙化时间长达两年,往后时间越久,粘连硬度越强。工地上,10口大锅下的熊熊火焰,蒸腾起翻滚的糯米粥,整个工程,共用去50吨糯米。
西昌,南方丝绸之路上名头响亮的重镇。作为城市诞生的历史,确切地从西汉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开始。汉称邛都,到隋唐称嶲州,南诏称建昌府,元称罗罗斯宣慰司,明为四川行都司,清为宁远府,民国称宁属。
古城,是古代文明起源的标志,它的兴废和变迁,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,经济文化的兴衰。西昌境内遗留有11个古城和古堡遗址。时代最早始于汉晋,最晚为明清。规模最大的是唐嶲州城,保存最完好者为明洪武建昌城。
邛海以东北的开阔坝子,即如今的西昌市区,古城分布相当密集,明清的三座古城仍依稀可见。
高枧汉晋古城,在西昌市区以东的高枧乡中所村。当地人称此城为“孟获城”。古城北临姜坡山丘,东、西、南三面地势开阔平坦,考古实测,古城呈长方形,南北长 373米、东西宽251米,城墙为泥土夯筑,四墙相合。除东城墙因修筑道路而局部受损坏外,其余大致完好。城墙上尚存十余处城堞。城墙残高1.8—3.6米,厚约5米。同时发掘出许多汉代砖、陶器残片等物,纹饰多系绳纹、弦纹和斜方格纹。专家们认为古城年代大约为汉晋前后,极有可能为三国时蜀汉大将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期间所筑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: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时“讨叛鄙,降夷人,安种落,蛮夷率服。嶷始以郡郛宇颓,更筑小坞居之。延熙五年(242年),乃还旧郡,更城郡城,夷人男女,莫不致力”。就是当时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修筑郡城的写照。
唐嶲州城,是唐代初期在西昌设立的嶲州都督府。唐太宗李世民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,鼓励发展生产,使西南地区的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,社会相对稳定。在此社会背景下,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嶲州城。这一古城至今尚陈布于西昌市区并跨越至郊区。城呈正方形,城墙为泥土夯筑,每边长约 1750米,残高1-3.5米,厚约14.5米,总占地约306万平方米。除南城墙因历年基本建设所毁外,余皆完整。嶲州城内除残存着唐、宋、元各个历史时期遗物外,明代建昌卫城又重建在嶲州的西北角上,其占地面积约为唐嶲州的四分之一。
据文物调查,嶲州城内外尚存重要遗址两处。一是唐代瓦窑遗址。在东城墙以东数百米处,窑为马蹄形,所生产的莲花纹瓦当与中原洛阳隋启官城内出土的瓦当别无二致。窑内发现唐开元通宝,证明此窑群属唐代无疑。瓦窑群生产的筒瓦、板瓦、瓦当等物,用之于城内建筑。二是唐景净寺遗址。景净寺为唐宣宗时南诏国景庄王母段氏所建,位于唐嶲州城西北角,后改为白塔寺。《宋史》卷四百九十六《黎州诸蛮》条叙,“山后两林蛮”于开宝二年(969年)六月“进贡”时,“由黎州(今汉源县)南行七日而至其地,又一程至嶲州。嶲州今废,空城中但有浮屠(塔)一。”今存白塔于清道光三十年(1850年)遭地震毁后,重建于咸丰九年(1859年)。塔为楼阁式七级砖塔,平面是八角形,底部周长14.8米,塔高21米,由基座、塔身、塔刹三部分构成,有无地宫不详。塔的第三层,八面龛内各有石刻佛像一尊,真像身披袈裟、秃头,脑后有背光,跏跌,神态端详,系唐代珍品。
至今保存最完好的,当属明建昌城了。
城市是市井生活的基础,古城也就沉积为历史的记录。
据嘉庆版《宁远府志》载,建昌卫旧城,“明洪武中建土城,宣德二年砌以砖石,高三丈,周围九里三分,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。后据北山,前临邛海,左带怀远河,右潆宁远河。四门:东曰安定,南曰大通,西曰宁远,北曰建平。”
这是说,建昌城始建于1388年,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。建昌城旧址位于西昌市区东北部,建在唐嶲州城西北角上。北与北山相结,西临西河,东有东河,东南为开阔平坝。与邛海相距5公里。明代建城时的北墙和西墙,完全重筑在唐嶲州城墙上,其走向亦相同。只是后来城墙东南角因遭东河水溢之灾,几经培修,边角略成弧形。故有人把建昌城形容为一把展开的折扇。
考古实测表明,该城在明代时为正方形,四墙各为1200米长,占地面积 144万平方米,现存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。城为砖石建造,以条石垫底再砌以青砖。城墙底部最厚处达20余米,高11米。城开有四门,南北东西相互对称。除西段城墙和宁远门早年被毁之外,其余三门尚存,城门上的年款为“洪武贰拾年四月吉旦立”。城墙上的纪年砖有万历、大顺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等。城内街道迄今基本保持明代布局,即以“钟鼓楼”(俗称四牌楼)为中心,向四方辐射。其北称北街、南称南街、西称西街(亦称仓街)、东称东街(亦称府街);另外城南有顺城街,城西有石塔街、三衙街、什字街,城东南有涌泉街。此外,各街之间又有20余条小巷相连,使各街巷纵横交错,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格局。
有意思的是,远在明清两代,政治、军事机关主要集中于建昌城东北部的北街和府街一带,故这一带的街道名称均与政治和军事相关联。如“都司堂巷”,因明代四川行都司衙门建在此处而得名,明代建昌卫署和清初建昌总兵衙门建在北街(今四川省彝文学校);清代宁远府府署建在府街(今凉山军分区修械所),城中“中营巷” “右营巷”“后营巷”即清建制军事机构“营”(兼管土司土目)的衙署所在。明清两代的文化、宗教建筑大多集中于城西的石塔街一带,其中久负盛名的景净寺、发蒙寺、关帝庙、城隍庙、云南会馆、陕西会馆、泸峰书院等,均分布在石塔街附近。
明清时期,南街、顺城街为商贸、集市的主要街道,贸易的商品以银铃、锡锭、金银饰品、铜器、生丝、白蜡、药材、裘皮等为特色。时光荏苒,今天的南街肯定比过往更加人声鼎沸,但它的功能没有变,街道两旁的小商铺摩肩接踵,尽管不如大商厦日进斗金,但眼见小商贩阳光般的笑容,也知道小日子的滋润。
从建城的手艺与匠心来看,先人的智慧一点不输城建师。
建昌古城在明清时期的引水设施比较完备,采取以引河水入城为主、掘井取水为辅,构成溪水长流、水井星罗棋布的引水系统。引河水入城主要有三处:城西北角“白塔寺”和城东北角“千佛寺”两处分别从北山引水入城,城东南的涌泉街“过水庵”旁引东河水入城,今西昌市二中(研经书院旧址)尚存明代“水仓”遗址。城内有明清古井,居民凡有水井者,官府统一规定在其大门上绘以“井”图样,为防火患利于取水。公用井中最著名的有北街明代“梅花井”、涌泉街明代“豆芽井”、石塔街的“大水井”、仓街的“胡家井”等,这些古井建造讲究,水源充足,水质优良,数百年不衰,一直沿用至今。西昌古城区排水系统也是渠渎纵横,依地势高低自北向南排水,主道为大水沟、苏家坡沟。
建昌古城几乎就是西昌历史的一个缩影。数百年来,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在古城上留下痕迹。“大顺”纪事砖在古城上被发现,证明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于公元1644年在成都建立“大西”政权后,其部将刘文秀(抚南将军)确在西昌举“大顺”旗号据城数月,同时主持培修了建昌古城。城内曾发现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过境情况的碑刻。北城墙上发现大量清咸丰元年(1851年)纪事砖,说明了道光三十年(1850年)西昌遭受强烈地震对古城墙的严重破坏,次年及时进行培修的纪实。
城墙的砌石和青砖都是可以触摸到的时光,但长途迁徙和漂泊一生的人们走进建昌城的时候,许多人选择了停下疲惫的脚步,开始生命中不一样的生活。炽热的阳光既给人温暖,也把未来的朗阔照得明亮。
沿着古道一路走来,我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举足轻重、又颇为有趣的的“点”上,只不过文字中表述的“点”并非单个数字的实指。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眼界,汉朝“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,就是行政单位叫作‘道’。道是一条直线,不是一个点,也不是一个面。从一条线,慢慢扩张,然后成为一个面,建立一个行政单位……汉帝国的扩充,是线状的扩充,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,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”。
尽管横断山东缘的群山叠嶂、江河湍急,形成重重阻隔,对外界事物的好奇一直是推动人类持续寻路与探索的原动力。只要你有过在连绵的山峦或者无垠的旷野目睹道路网络般的延伸,你就会对此深信无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