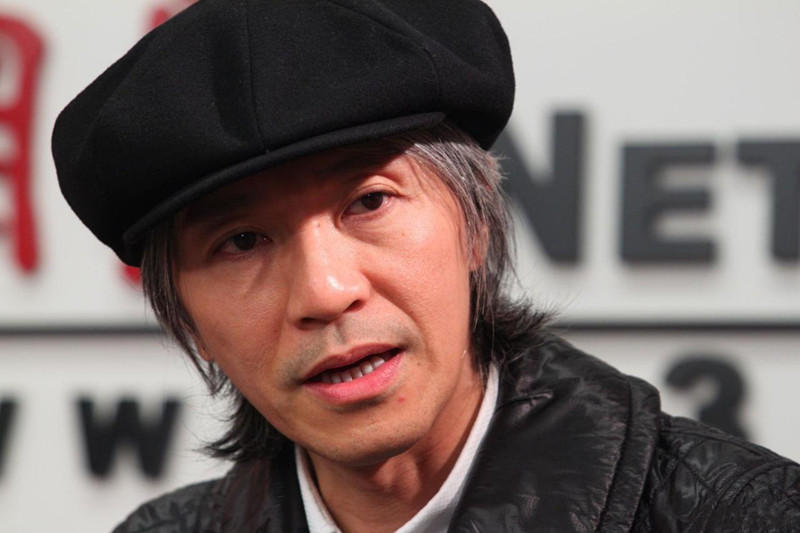彝地之首 ——加拉巫沙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9年第一期
- /
- 作者:加拉巫沙
- /
- 2019-05-24 11:41:11
- /
- 24
- Views
一
文明的孕育多与河流有关,流向哪里,哪里姹紫嫣红。即便是被峡谷逼迫得汹涌呼啸的河流,大抵也会出现平缓的河段,经年累月地流淌,与人的创造力一旦媾和,文化和文明就灿然了。
大渡河,由藏区跌跌撞撞而来,凶猛急速,似有把高山冲毁、崩裂、垮塌的磅礴之力,但进入甘洛以北,像被驯服了,波光粼粼,蓝幽幽地流淌在宽阔的大山河床里。流域南北可望,但毕竟山高水深,天堑阻隔,两边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哪怕很迫切,也得绕山绕水慢慢地来。这条大河,巧妙地设置了地方治理界限、不同民族分布、多元文化生态等等的障蔽,于此意义上,河流成全了整个流域汉、藏、彝等民族的文化,即是文化冲突的疆域,也是文化杂糅的走廊。
万重山水,万重险阻。一个民族的地域文化还想跨过大渡河,继续北飘或者南飘,那一定担着风险,文化的张力即使假想成子弹,多飞一会儿,估计也动能不足,气数将尽。若以彝族自观,先民把一亩三分地开垦到大渡河边后,望见巨龙般奔腾的河流,摇摇头,一声叹息:就此止步吧!停下北伐的脚步,并非已经没有了欲望和激情,天堑地理的发现,令人不寒而栗,借一百个胆子也借不到飞翔的翅膀,横空而去。
对于一个诗性的民族,放牧牛羊可能跟放牧诗歌没有多大的区别,从一开始,凡涉及甘洛这块地域的诗性谚语总以“首”和“大”被凝练、被颂扬,奇怪的是,以老大自居的认知尽管桀骜不驯,却得到了南方彝人的首肯:甘洛,彝地之首。的确,从四川西南一路往南,直贯云贵高原,彝族密布,彝人生息,而甘洛端坐北方之首,可以俯瞰一切。
彝谚“彝地甘洛首、汉区官府首”不单舞蹈在嘴唇上,它还以经文的姿势涌动于古籍的汪洋里。既然是“首”,并非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古代甘洛,其文化又怎么建构呢?《天神地祇书》《万物起源书》记载的天神、地祇,居于甘洛的个头最大、力量最强,威力无比,哗啦啦下至滇北的毕摩和苏尼做法时,不得不诚邀甘洛的神灵冲锋在前,捉拿妖孽,而甘洛的各路神祇总是耳提面命、左冲右突、披肝沥胆,誓死捍卫着万千彝人的宗教健康。
一面是鬼神的玄说,一面是地理的奇异,真要置身其中,虚虚实实的,还有些让人不安、惊抖和恐慌。境内山峦林立,其中的四十八座山皆有彝名,也特著名,都有各自的山神严严实实地守护着,最著名的德布洛莫山和吉日波山不仅活在一隅的高耸里,而且还活在川滇彝语北部方言区《鬼之起源》、天地演变史《勒俄》的诡异里;入选中国十大最美峡谷之一的大渡河金口大峡谷,雄伟壮观,险峻幽幻,德国人豪格尔·帕奈看一眼就惊奇万分,上帝啊,这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多么相似!
发现的眼光不在当下,而在远古,在历史的深处。
视甘洛为通向异域的门户,不是一个族群的独立发现,面对滔滔江水,两岸的人们在心里划出各自的警戒线,这一划分即是地理的、也是文化的。你看,在“掠蜀为奴”的彝族古代社会里,唐代诗人雍陶哀叹:“大渡河边蛮亦愁,汉人将渡尽回头。此中剩寄思乡泪,南去应无水北流。”他还吟唱:“冤声一恸悲风起,云暗青天日下山。”
大河横亘,天然地把南北族群以及文化对立起来,文化的对立又终究带来政治的冲撞,带来社会的动荡和祸乱。
好在历史的负面早翻页了,迭代它的是新中国崭新的政治篇章,大渡河流域开明开放,欣欣向荣,如日方升,书写着一幅经济共兴、文化共振、情感共鸣、民族共进的时代画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