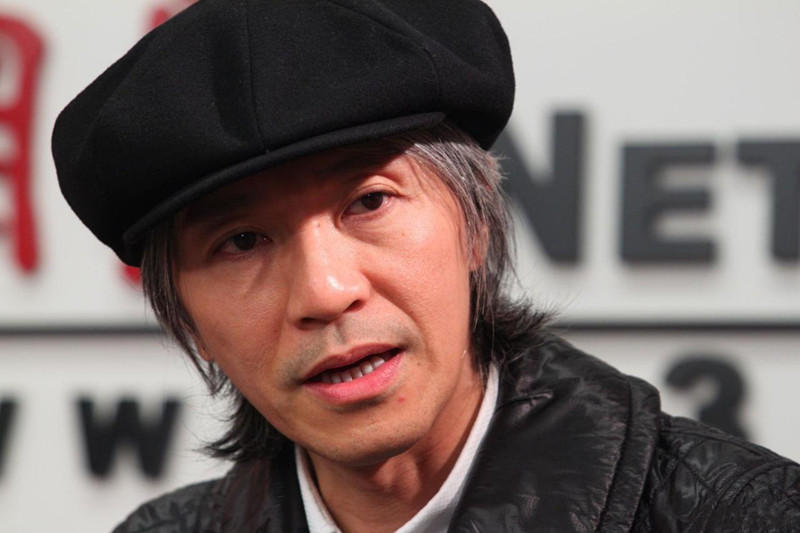彝地之首 ——加拉巫沙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9年第一期
- /
- 作者:加拉巫沙
- /
- 2019-05-24 11:41:11
- /
- 24
- Views
三
犹如阿拉丁神灯的寓言,很多甘洛人因为铅锌一夜暴富。
曾经的甘洛城是不夜城,灯红酒绿,声色犬马,穷尽繁华!一个个暴发户,来不及细细思量,挣钱了显摆,显摆后挣钱,人都横着走。给横着走的人谈论文化,有些不合时宜,充其量文化是装点门面的道具而已。依我判断,昔日的甘洛人很少关切自己的文化,可能连试一试的想法也未曾有过。是的,在一个钞票飞舞的年代,全民疯狂淘金,资本的宴席上还设什么文化的座椅?文化谈论得再热烈、再急迫,也只在私下,公众面前抬不起头来的。而今,埋藏在地下的铅锌矿价格一落千丈,甘洛回到了本真,恢复了原本的秩序,但人的心态显然已经无法适从了。
甘洛人集体陷入慌乱、惶恐、焦虑、浮躁的一个新时期。
那么,该如何安抚内心、安顿灵魂呢?
回归到秩序当中来,也就回归到了人的理性思维上,拂去蒙尘,彝地之首的文化还温热着呢!像当年的淘金梦,甘洛开启了文化的追寻之旅:要打造一个地域的文化,还得往历史深处去寻访。
对了,追逐经济天经地义,但把自己从头到脚金缕玉衣地包裹,不是像一个即将掩埋的陪葬品吗?正向的文化不像经济,再怎么包装和塑造,它撼动和感召的是人之心灵,是希望,是未来。
近些年,甘洛公祭吉日波,还郑重其事地邀请过我两回。
唤作吉日波的山,不高,金字塔形,看起来更像一个锥形的小山包。彝族天地演变史《勒俄》中记载,洪水滔天之际,周遭一片汪洋,举目四望,只有甘洛吉日波、伙姆顶册波、艾叶安哈波、蒙地尔屈波等大山露出了尖尖的山头,挽救了人类和动植物。我无意刁难甘洛人对古籍中圣山的集体指认,滔滔洪水湮没大地,旁边众多高耸入云的山已被淹没,为什么矮小的吉日波还能显露奶头模样的山顶?文献里的彼山是否另有所指?人们对经典的甄别是否缺乏反思的能力?
但甭管怎样,以文化的视角公祭一匹山,其实是甘洛人在公祭彝族历史文化的同时,也公祭了全人类诺亚方舟式的远古传说。
问祖先,问历史,到底追问的是文化和自我的心灵。
那座叫德布洛莫的山,横跨甘洛越西两县,彝人的先祖对它觑觎已久:那里,不是离腹心之地遥远么?何不把作崇人的家鬼流放到德布洛莫去?文化的意义上,早期的鬼山不在此地,而是在云贵高原的某座山上,祖先可能受到神灵感召,一下子把鬼域迁徙到了领地之首的德布洛莫山。这里,彝族先民像历朝帝王流放罪犯一样,惹恼了,把鬼怪驱赶到天之涯的边疆,让鬼魅些类聚,再说,甘洛的天神地祇历来威武,势力庞大,可以严加管控妖灵。
地理的险恶,文化的边缘,不把鬼怪驱赶到这里,难道还安顿它处?
也源于此,甘洛便注定成为“鬼神之都”,上千年地被诅咒,上千年地被颂扬,上千年地被膜拜,生生地活在鬼神文化大一统的彝人世界里。
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件文化大事。若以传播价值换算,在广袤彝区里,还没有哪个县有甘洛如此幸运!不花一分钱,却被数百万彝家儿女心里念着、嘴边叨着,永驻在彝族人万物有灵的信仰里。于此意义上,甘洛是多么重要的彝地之首,除地理之外,又是文化的、又是宗教的。
“鬼神之都”的甘洛人自然也就成了鬼神之主,遛达时,牵的不是毛绒绒的狗,而是具象的鬼和神。续以遛鬼和遛神的假想推理,公祭吉日波的由头可能小了些,一时半会得不到整个彝区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,自娱自乐尽管已经够好了,但怎么地也是自己演给自己看,朗朗的经声没能指引更多普罗大众前来洗礼。那么,换一个噱头如何?把德布洛莫的鬼和吉日波的神由虚变实、由幻变现,把林林总总的草偶、泥偶、鬼板、神图做成与人等身的工艺,最好还给三脚的鬼神装上呼呼生风的轮子,与人共舞,与民同乐,做足人鬼、人神那千年未了的文化命题;至于声若洪钟的祈福经声,能否选段刻制成激励孩子读书之用的戒尺,或者汽车的某个挂件;毕摩肖像以及他们使用的法器又能否雕刻成旅游商品,投向南方,所向披靡……
如是,四海彝人将朝圣般涌来,他们并非来探视那些具象的鬼怪和神灵,而是来探寻文化指向的坚定,为什么一个民族对天地、历史、万物、生死的哲学回答如此神秘?它对拯救心灵究竟起着什么样的鸡汤作用?为什么物质贫穷的个体精神却如此大富大贵?真要探寻到了润泽心灵的文化瑰宝,民众还有什么理由去怨天尤人,而不去奋斗?
只怕,甘洛喧闹一阵,最终像风一样飘散。
那么,能够定夺文化命运的人且抽身去趟鬼城丰都吧!去见识汉语语境里的草根意识和艺术观念碰撞的“地狱”,想想人的灵魂需要什么样的方子才能救赎,才能安身立命,才能昂扬向上,进而热爱生活、敬畏生命。
打开鬼神这道门,彝族的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教育、哲学……都静候在里面,啪掉尘埃,拿着的哪一部经卷不价值连城?
我以为,只要人不神神叨叨,坐拥彝族鬼山的甘洛应往前迈进,缔造出集传统鬼神文化与现代声电光技术为一体的“鬼神王国”。
在彝地之首,遇见有趣的精灵,穿梭在人鬼神之间,那一定是关乎地理、文化和宗教的令人颤粟的惊艳。
在彝地之首,重要的不是对着鬼神祭祀了什么,而是把鬼神当作民族文化的敲门砖和大众娱乐的因子,洒脱地外递一张文化的名片。
在彝地之首,甘洛人探询到的不单是自我心灵的隐秘,恰是一个族群内心的普遍性隐秘,像一面镜子,不仅映照出彝人文化的原貌,而且也可让他人走进神秘文化的涌流,窥见自我心灵的一些影子。
永不停歇的经声飘飘渺渺,我们应当把它理解为对生活的诵唱和对生命的礼赞,理解为大渡河南岸的甘洛人收敛了性格中的自大、伪诈与浮躁,正驾驭着大文化的帆船乘风破浪,驶向彼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