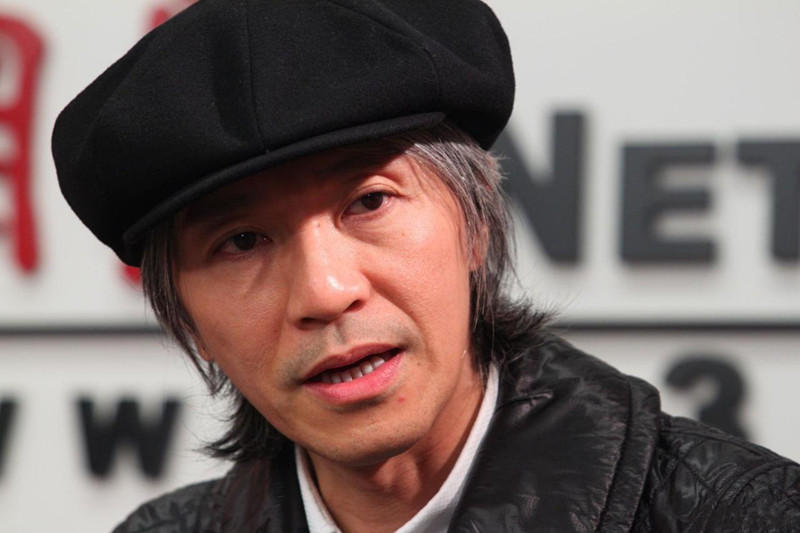彝地之首 ——加拉巫沙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9年第一期
- /
- 作者:加拉巫沙
- /
- 2019-05-24 11:41:11
- /
- 24
- Views
二
甘洛的文化庞杂,是大渡河流域典型的文化杂糅区,非马非驴也非骡子,都像,又都不像,自我酝酿着,七零八落地形成区域的特色。
向来,甘洛人自恃清高,给人居高临下的印象。此等感受在人际关系处理上时时显露,综合研判的结果是甘洛人偏好标新立异,真真假假地,他们“得意忘形”,以为自己的观念最前卫、生活最时尚、礼仪最得体和文化最先进。
甘洛人的汉语发音是乐山话的翻版,完全脱离了地缘政治上大凉山人的语音。完整的对话里,有句与“鸡”相关的不时拿出来戏谑:“哪里鸡?”“田坝鸡。”“鸡咋子?”“鸡买鸡!”除尾音的“鸡”是要买的鸡之外,前面的“鸡”皆为“去”的意思;又来听彝语的发音,田坝一带的彝人不多,但他们创制了北部彝语方言支内的田坝土语,还辐射到紧邻的越西、峨边、汉源等县的个别区域,说话像歌唱,柔柔地拖拉,“迪比……迪比”,不紧不慢地吐纳。
据传,耕作于矮山平地的彝人养彝语叫“丝”的蛊,将毒蛇、蝎子、蚂蟥、蜥蜴等放进器皿,使其互相残杀、啮食,最后存活的毒虫便是蛊。表面上,它是有形之物,但自古被认为是能飞游、变幻、发光,像鬼怪一样来去无踪影的神秘之物。养蛊者,多为妇女,有客进门,一旦蛊“噗噗”闪亮,妇女便与它沟通,给谁下就得下,否则,妇女或者其家人就必须派一人吃蛊,一命呜呼。还说,蛊也不是成天毒人,但每年不毒死一人,蛊也非蛊了。毒人,不是立马倒地,下毒后,吃蛊的人肚子里长虫,像蚂蟥尸粉,进入肠胃,活脱脱新生,说得很恐怖。子虚乌有的传说吓唬过我,那些年头,我在玉田中学读书,路过同学父母的寨子,再怎么热情地招呼,我等勒紧饥肠辘辘的肚皮,笑嘻嘻地远离。活灵活现地编造,把一顶最毒妇人心的帽子扣在了女人的头上,足以说明甘洛一带的传统社会局势多么动荡,他们进犯别人或者别人犯难他们之时,都留有杀手锏:别惹我,哪天我会毒死你!甘洛人明知以讹传讹,却永远不捅破,含含糊糊地,都以为他家里的蛊梦幻般地蛊惑人,保不准你是它喜爱的那一口。
甘洛人狡黠、浮夸、狂傲的文化根源可能与大渡河流域文化和经济互通互融有关,不来点奸诈,容易被人看穿底裤是什么颜色,威风扫地;也可能与养蛊和鬼神的玄说有关,毕竟这些讯息太神秘、太奇异、太狰狞了。像一个人说自己有盖世武功,看他身体那么壮实,帮腔的人又佐证无数惨烈,你何必去招惹自吹的这个人呢?吹牛的面子一破,不狠狠揍你才怪。
甘洛人在饮食、娱乐和精神上还要另类!
一种生在密林树干上的“玛玛菜”摇摇晃晃地悬吊,甘洛人捣鼓几下,端上桌,蛮好吃的。“请你来喝杆杆酒,请你来吃玛玛菜”,濡染南丝路文明的甘洛人深情歌唱,外加一句“牵着马儿等你来”,外人心里猜测,真来了,他还牵着马翘首以待?玩笑而已,嬉皮而已。在交通占位上,他们北上省会成都和南下州府西昌差不离,但动辄爱往北方走,感觉上与省会人平起平坐,脊梁挺得很直,与南下的州府人见面,狂傲是藏不住的,即便内虚,见多识广的模样摆得同样离谱,把别人当傻子看呢!子女读书、家庭买房依然一路向北,抵达不了成都,也要把起跑线划定于乐山,连做梦都朝着繁华的都市梦去,醒来还以为检了个大便宜。哗啦呼啦的麻将打起来,专业术语叫“甘洛麻将”,钱“噌噌”翻倍,算法又有别于成都的“成麻”,压根不屑于攀西地区习惯开打的“攀麻”。
向成都看齐,近乎成为甘洛人的宿命,别人没有张开怀抱,他们硬要钻进人家的被窝。
对外的甘洛人,角色转换收放自如,见什么人演什么角,仿佛天下是他们的。面对侃侃而谈的甘洛人,以为他们太精明,心里上准备要防范的档口,他们又把彝族人耿直、豪放、爽朗的性格展示两招,弄得外人两难,莫衷一是。文化的杂交,并不都指向优秀,也并不都指向拙劣和平庸,大渡河孕育的杂文化刚柔并济,润物无声,却奇特地反映在甘洛人的精神世界里。
对内的甘洛人,喜欢窝里“斗”,换句好听的,就喜欢划圈子,划来划去,最大的圈子可能是由历史习俗差异导致的地域人群的划分,两大群落“诺姆苏”和“曲姆苏”桌面上握手,桌底下使绊,好在没有“绊”出什么大事,像兄弟姊妹,磕磕碰碰,终究还是一家人、全家亲。前者,强调身份的纯粹,一般居于高山,操北部方言;后者,突出文化的进步,住地平坦,适种水稻,操田坝土语或腔调拐来拐去的没有被命名的小土语。两大集团谁也瞧不上谁,内部又细分,把乡镇区划纳进去,复杂得像雾里看花,灰蒙蒙一片。“曲姆苏”得意,曾有“自由民”的历史身份,谁都管不着,谁也不敢管,不赋役,不纳粮,自由啊!“诺姆苏”立即反驳,没人管意味着没人罩,被人打了,还有人替你打抱不平吗?没有组织的队伍不是团队,只能是团伙,群龙无首,纵使每条龙有遨游九洲的本领,终究也是一条虫的肚量。两者的辩论由历史而现实、由社会而政治,时而同盟,时而分野,煞是有趣。
诚然,就整体的综合地位而言,凭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“曲姆苏”跃上了高一级的社会台阶,“诺姆苏”则紧随其后,奋力攀爬,共同推进着甘洛的文化成熟。这里,还有两股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,散居于多个乡镇的尔苏藏族,戴着白色头帕,穿着花衣白裤,悠扬地踏歌而来;那些由溃散的太平天国军人演化而来的彝人,文化更加纷扰,但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,一代代视甘洛为故乡,早已梳理出可以兼顾和通融的新彝人文化。
甘洛的文化就这么兼收并畜,可真到了文化凝练的关口,清高与倔强又出来坏事,各说各理,各唱各调,统揽不到一起,唯对整个彝区认可的宗教文化无反驳之力。依我理解,甘洛县域内的庞杂文化即使自己给自己戴高帽,也荣光不到哪里去,但涌动于浩瀚的古籍和彝谚里的那些宗教文化,却能对彝地之首的文化重塑大有裨益,只恐甘洛人看见诺多的“首”和“大”,又犯好大喜功、好高骛远之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