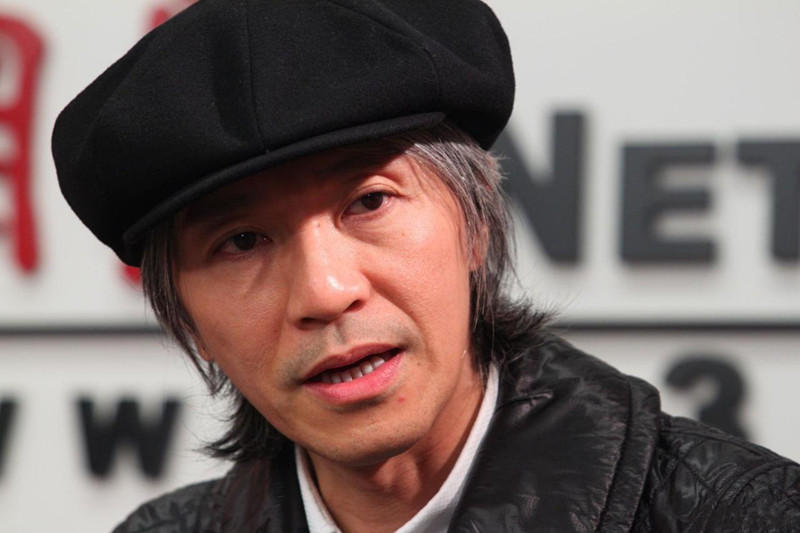古道苍茫 ——何万敏
- 来源:《凉山文学》2018年第二期
- /
- 作者:何万敏
- /
- 2019-05-24 12:07:19
- /
- 24
- Views
走清溪道
思绪仍然要到泛黄的地图上去查看,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迷人曲线也是由北向南的。汉称牦牛道、灵关道的西路,从今天的雅安市汉源县富林镇南下,走进四川省“凉山北大门”甘洛县。只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,这一段路因穿越清溪峡而取名为“清溪道”。
史书上也还没有甘洛县的称谓,汉武帝开始在凉山设置郡县时,甘洛这方属越嶲郡辖。而甘洛建县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12月11日。
河流成为方向,峡谷即是良好的通道,导引着人的旅程,避免误入群山的迷宫。
问题是,南方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必经凉山的这一段,“从汉代历经唐宋乃至元明清,始终处于一种规律性开闭状态中”,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馆长邓海春的观点是,“中央王朝强盛时,道路能开城设驿保证畅通,一旦中央王朝到了末期或实力衰落,边疆少数民族势力又强大后,又处于封闭阻隔状态。如此循环往复,一条古道,就会在不断的战乱中湮灭于历史谜团中”。
不妨翻阅史书上的蛛丝马迹。多年来,对清溪道城驿有过考证的邓海春认为,唐人樊绰所著《蛮书》中记载最为详细,并且又以向达校注的此书最为确切。他拿出中华书局1962年版本,翻到这里:
“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,州、县、馆、驿、江、岭、关、塞,并里数二千七百二十里。从府城至双流县二江驿四十里,至蜀州新津县三江驿四十里,至延贡驿四十里,至临邛驿四十里,至顺城驿五十里,至雅州百丈驿四十里,至名山县顺阳驿四十里,至严道延化驿四十里。从延化驿六十里至管长贲关。从奉义驿至雅州界荣经县南道驿七十五里,至汉昌六十里,属雅州,地名葛店。至皮店三十里,到黎州潘仓驿五十里,到黎武城六十里,至白土驿三十五里(过汉源县十里),至通望县木良驿四十里,(去大渡河十里)至望星驿四十五里,至清溪关五十里,至大定城六十里,至达士驿五十里(黎、嶲二州分界),至新安城三十里,至箐口驿六十里,至荣水驿八十里,至初裹驿三十五里,至台登城平乐驿四十里(古县今废),至苏祁驿四十里(古县),至嶲州三阜城四十里,(州城在三阜城上)至沙也城八十里……”
可能有些枯燥了,但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勾勒出,遥远时代清溪道的走向。邓海春解释,唐时的一里,约等于现今的540米,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城驿之间的实际距离。
古道依旧蜿蜒,暗示着时间的久远。
循着马夫的汗味与马匹的蹄印,2014年立冬时节,我来到清溪峡南端的甘洛县坪坝乡。“想去深沟,阿啵,我太熟悉了。”帅气的乡党委书记罗阿木执意要陪我去。这位43岁的彝族汉子所说的深沟,就是指清溪峡。他1990年3月招聘到坪坝乡做计生专干,对这一带山水相当熟悉。他称自己“工作25年一直在坪坝、前进、大桥”三个乡。由于坪坝乡远离县城,海拔较高,冬季十分寒冷,农作物以马铃薯、玉米、苦荞为主,当时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两千元,但他强调:“老乡很淳朴。”
罗阿木同样踏实,帮我拎起摄影脚架就上路了。乡政府所在地是坪坝村三组,一条古街径直连接着古道。说古街,其实不尽然,约两百米长的街道本是用混凝土铺面的,却因当作燃料的干枯蒿草,和背兜、摩托车随意摆放路边,加之前几天的雨水流淌一地,留给人一些零乱的印象。古意犹存的是街道两边的房屋:低矮的屋檐仿佛支撑不起发黑又泛着天光的青瓦,斑驳的土墙与石墙脚底普遍因雨水侵蚀已附着一层绿色苔鲜,家家户户的陈旧木门板多数门锁紧闭,若不是看见金黄的玉米棒子垂挂在屋檐下,或者有些木门上还贴着红底金字的春联,我实在怀疑村庄已是人走屋空。偶尔见到一位白发太婆坐在家门口的木椅上歇气,她头戴绒帽,棉袄外罩着紫罗兰色上衣,双手向上摊着,手指似乎沾着什么,像刚做过家务事还没有来得及清洗,微笑着任我拍摄。我还见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在洗涤一盆红色的、粉色的衣裳,一旁幼小的孩子身背玩偶、手端彝族漆器的饭碗在吃午饭。村头以及街道中段许多处,扎眼的是已破败并遗弃的木屋、土房,默默积淀那些曾经鲜活的故事。
经过一片开阔的草地,清溪峡就在眼前。
当层叠的青山分列两旁绵延而去,伴随一条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流,泛着光亮的青石闪露于绿黄色的草甸间,我知道,这就是清溪峡古道了。而挟持清溪向北奔流耸立两旁的山峦,所组构成的当是清溪峡。
不用说,走进峡谷,本来已是清洁的空气更加清冽,沁人心脾。茂密的植被覆盖着群山,天气寒冷的缘故树木长不高大,季节正开始把铭黄、橘黄和绛红泼洒上绿叶枝头,缤纷的颜色悠然透过云层的阳光照耀,亮丽而令人心旷神怡;踩踏在铺满深褐落叶的古道上,清脆的窸窣声与凉爽的流水声相应和,音乐旋律般回荡于峡谷。当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声音听成马帮铜铃的叮当,或者穿越时空的历史跫音像一个幽灵在溪流上飘浮。绝壁处是凿空的甬道,行人得低头勾腰,不知道当初马帮怎样能够通过——难道好久没人从这儿过,沉重的山体又压下来一截了?有几处坡陡弯急,道路右下是悬崖,步步惊心不敢大意。从崖缝中生长的小树,伸枝展叶凸显坚韧顽强的生命力,也快要挡住行走。走到峡谷深处,树木愈加长得浓密,仰望山顶的森林竟有原始的模样。如影随行陪伴着古道的清溪层叠而下,奔突婉转于巨石之间,跌落成乳白色的流水美得像刻意雕琢的风景明信片。一路美不胜收,只顾按动照相机快门,也就忘了疲劳和困顿。
徒步两个多小时,到一大跌水处,道路改至右岸,我跃跃欲试,想跨越过去继续前行。估计跳不过去,罗阿木也婉言劝告,说若摔下那几个块被水冲得光滑的巨石会很惨。脚下是河溪左岸建有小型水电站的引水渠,据说已舍弃不用,此处原先搭建的便桥也不见踪影。石上仍有依稀可辨的马蹄印凹痕,我有些依依不舍,想象着路途的艰辛,只得遗憾地返回。《甘洛县志》有文:“清溪关是唐贞元十一年(799年)川西节度使韦皋为和吐蕃通好南诏所设关隘。清溪峡为南北走向,全长5公里,南起甘洛县坪坝乡政府驻地,北至汉源县的大湾。”此文明显有误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贞元十五年(799年),“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嶲州,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;吐蕃无功而还”。当天我走了6公里未到目的地,所以我觉得另有资料上说清溪峡甘洛段长约7公里,至大湾约10公里,比较可信。
我还感兴趣的是,在折返走出峡口的河滩开阔处,偶遇十几匹建昌马悠闲地在草地上晚餐。这些建昌马中除有3匹为粽黑色外,其余全都是粽褐色,嘴唇均为浅白色。它们背脊处两边各有两处鬃毛被磨得可见皮实,那是驮运物资劳累摩擦的印迹。做人不易,何况任由人支配的马匹。中国原生马种分为五大系:蒙古马,河曲马,西南马,藏马,哈萨克马。其中,西南马系统身材最矮,建昌马又是西南马系统中最矮的一支,成年公马平均体高为1.2米左右,也就与成年人腰部差不多。别看建昌马体格短小精悍,它们吃苦耐劳、善于跋山涉水和长途驮运的美誉,也算赫赫有名。建昌马也当仁不让地成为西南丝路灵关道上的绝对主力。
除了从甘洛县坪坝乡向北至汉源县大湾,清溪道更长的一段是坪坝乡一路南下至蓼坪乡白沙沟,全长达48公里。明清时,这一路段设有坪坝、窑厂(古新安城遗址)、尖茶坪、海棠关、镇西、清水塘、腊梅营、蓼坪等关、铺。如今,这些地名在1:200000的甘洛县地图也找不到几处,更不要奢望发现什么有价值的遗址。但我知道古道等待着我,我没有理由不去走一回,即使从坪坝经海棠镇再到蓼坪乡的古道大多筑成公路,也只得驾车缓慢在山间起伏间寻觅。所幸海棠古镇尚留有许多材料供我下一篇文章专门讲述,太多遗迹已随岁月和季风散尽。
在时间深处,古老的文明消失于星光闪烁的夜空。
现为凉山州博物馆馆长的唐亮,2006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,曾率领凉山州和甘洛县组成的文物普查队,背着干粮和设备,沿途用GPS定位仪器测量,用数码相机记录,徒步5天时间,理清了一路的驿站、营房遗址、青代石桥、清代墓葬群等等。“这就是全新的线性文化遗产,不是孤立的一个点,而是形成了一条线。”唐亮当时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。
所幸,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心血浇灌出结果。2013年3月,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“甘洛清溪峡古道”名列其中。
随后,在清溪峡古道南口,可见甘洛县政府置大理石碑,碑文明确了古道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:南北自双石包至横岩子的水源、植被及青石板路面,全长5公里范围内;东西方向以20米范围为界。该范围东、西外延至峡沟两边山峰为建设控制地带。
清溪峡古道升级以前,零星有驴友慕名而来,体验远古的清风侠骨。据说南京大学旅游学院20多个师生来此调查,号称受富商委托搞开发前期规划。甘洛县城建和旅游方面也设想投巨资加以开发,但不菲的资金成大问题。
平坝乡党委书记罗阿木也忧愁经济的增长。甘洛县是凉山黑苦荞种植基地,全县一万亩的种植面积,坪坝乡就占到一半。他成天焦虑的是贫困农民脱贫攻坚“战域”的大事,还没有精力去打古道发财的主意,无法顾及古道上五颜六色人来人往的浪漫想象。